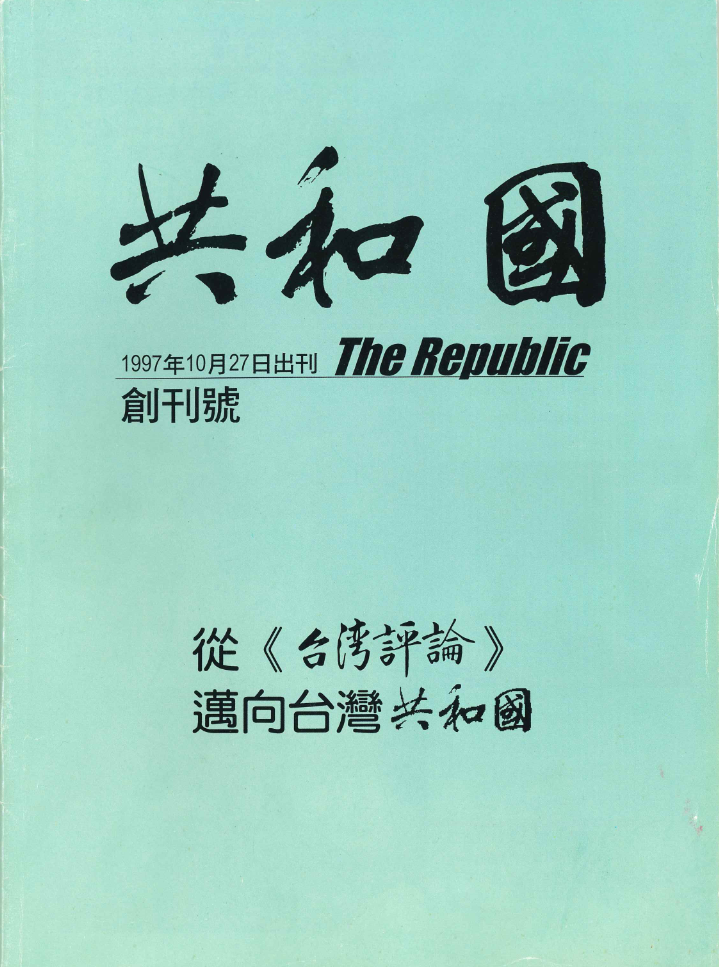公民投票入憲的意義
最近蘇格蘭及威爾斯舉行公民投票,以決定是否設立獨立議會及擁有部份地方自治權。最近幾年來,世界各國以公民投票決定國家重大事務或公共政策的例子甚多,如一九九四年阿爾巴尼亞公投通過採用新憲法,波士尼亞境內的塞維亞公投拒絕接受國際和平案,一九九三年馬拉威公投廢止一黨專政建立多黨制,巴西公投決定維制總統制,俄羅斯公投通過社會經濟改革案,意大利公投採用新選舉制度,一九九二年愛爾蘭公投決定墮胎合法案,加拿大公投否決修憲案,丹麥、愛爾蘭、法國、奧國、芬蘭、瑞典、及挪威公投決定是否加入歐洲聯盟……等等。這些例子顯示公民投票制度是世界的潮流。 公投之蔚成世界潮流最根本的原因是代議制度是間接民主,也是菁英決策,往往與民意有高度落差,尤其選舉制度如不健全時,代議制度會產生甚多弊端。為了彌補代議制度的不足(而不是取代),直接民主式的公民投票自然成為現代民主國家的決策機制。國人對於公民投票似乎尚有嚴重誤解,尤其執政的國民黨對它更是有太多疑慮。四年前立法院即有公民投票法草案的提議,至今仍因國民黨的反對而未能通過。據筆者所知,國民黨反對公投立法最大的原因是,它只是「創制複決法」而不要「公民投票法」,而且實施範圍僅限於地方自治事項而不及於全國性事務。 其實,將公民投票與創制複決分開是對公民投票的誤解。創制與複決只是公民投票的形式之二。創制複決是對法律的公民投票。其他的公民投票形式有對憲法(制憲與修憲)的公投,對國家重大事項或政策的公投,這些形式的公投在其他國家行之有年而且頗為頻繁。只實行創制複決而不實行全面公民投票是對「主權在民」的折損,尤其在多元民主的世界潮流是一個開倒車的現象。 因此吾人認為現行憲法第十七條規人民只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及複決權是落伍陳舊,違背現代主權在民原理的,尤其第廿七條將中央性的創制複決,交由中央民意代表機關--國民大會行使更是違背公民投票,應由公民直接行使的原理。因此吾人認為這兩條憲法條文應加速修改,以符合現代民主趨勢。 今年修憲過程中,民進黨原先堅持公民投票入憲,後來因修憲政治妥協,與國民黨簽定同意書在「下次修憲」處理,令人感到遺憾,也令人感到疑慮下次修憲是否真正會優先處理這個問題。在學理上,公民投票的權利是主權在民原理下的必然權利,不必在憲法上明文規定才能實行,但現行憲法有上述違背主權在民原理的規定,吾人認為應該儘速修憲以匡正其謬。 至於公民投票法的立法,在程序吾人認為在公投入憲後再行處理,在法理上比較週延。但是並非有公民投票法之後才能舉行公投。在其他沒有公投法的國家,常以特殊立法(AD HOC.)的方式,例如訂定一個「公娼制度公投法」來決定公娼問題,或是根本不必立法由政府自動舉行某事項或政策的公投。前者既有法律根據自有其法律所規定的效力,而後者則有政治上的約束力,一個有責任的政府(RESPONSIBLE GOVERNMENT)當然是要遵守的。 吾人希望執政黨及在野黨都要重視公民投票的重大意義,儘快將公民投票納入憲法並制定公民投票法,使公投制度早日建立,融入世界民主的主流。